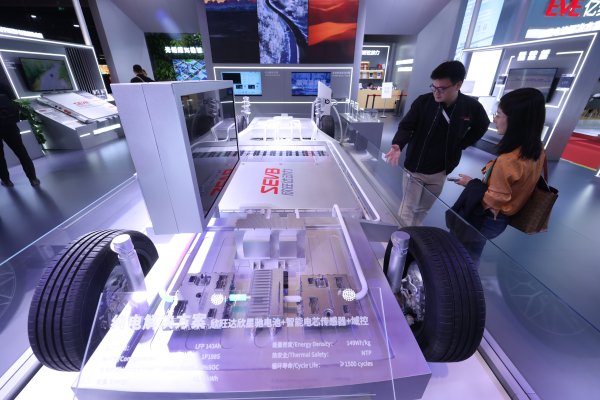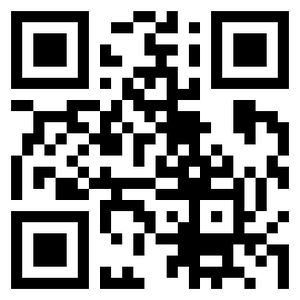“白毛浮绿水”用沪语怎么吟诵,字正腔圆飙出“冰灯钉鹰星”,“鼠目寸光”用沪语如何发音,这是上海滑稽剧团针对5岁到12岁少儿举办的沪语文化普及活动。
“外国有pizza,上海的葱油饼邪气嗲”,大鲸鱼欢唱团小朋友用沪语歌声赞美上海美食、拍摄MV,这是荣威·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办《侬好,囡囡》上海童谣亲子音乐会推出的彩蛋。
当飞机、公交车、地铁、剧院响起越来越多沪语播报,沪语《长恨歌》《繁花》年年与观众相约话剧舞台,当滑稽演员、沪剧演员每次露面,都有观众讨论他们的新作,每个沪语博主视频都被网友“咬文嚼字”品评,还有一群人,一直坚持教上海小囡说上海话。
把面前的纸打穿,嘴皮子才有劲
上午10点,又一期沪语文化研学活动在静安图书馆闻喜路馆开始。当天课程以“上海美食”为主题,家长带着孩子坐满图书馆214室小舞台。
上海滑稽剧团演员赵灵灵不急着讲课,他先提出要求,“从第一排的孩子开始,每个人都站起来,用上海话说自己的名字、几岁、读几年级。”有孩子嗫嚅着不动,有孩子左顾右盼找家长求助,也有孩子毫不羞涩“抢”话筒。

 每个孩子都要用沪语做自我介绍
每个孩子都要用沪语做自我介绍
不少上幼儿园的孩子,每说一个字都会卡壳。赵灵灵耐心指导,“上海话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眼睛看嘴型,耳朵听发音。”孩子懵懂重复他提出的“侬几岁”,而不是回答问题。家长们乐成一片,举着手机抓拍,“如果小孩上海话流利,我也不带他来上课了。”
一轮自我介绍结束,孩子们明显情绪轻松了。赵灵灵端上当日“正餐”——用沪语解锁《上海小吃》。不止于上海早餐“四大金刚”,还包括水晶包、条头糕、定胜糕、八宝饭、莲心汤等,孩子们都要学会清晰用沪语表达,上台展示。任务挑战现场,图书馆安排趣味“研学任务卡”,完成情景模拟任务,盖印章,课后获得阅读小奖品。
“我们需要‘社牛’小朋友,大家给他点掌声,好不好?”动员完台下大小观众,赵灵灵鼓励第一个上台展示学习成果的潘昊霖,“咱们先呼吸一下,放松,不管下面坐的是谁,看着墙上的字,用我们刚才练习的方式说一遍。”
 赵灵灵走下讲台,与小朋友互动
赵灵灵走下讲台,与小朋友互动
潘昊霖深吸一口气,“哎呀呀,我眼花绿花看勿光,再从头到尾唱一遭……”赵灵灵轻轻拍手,示意孩子们拍手跟读《上海小吃》,“在掌声节奏里,我们把绕口令说出来,把嘴皮子动起来。上海话发音在口腔前面,我们小时候练上海话,面前放一张纸,把这张纸打穿老钱庄,嘴皮子才会有劲。”底下有人交头接耳,“我也找一张纸喷喷看。”
学习沪语绕口令,从“四大金刚”探究上海早餐文化,只是课程第一层;“阳春面”为何叫“光面”,“两面黄”又是什么,挖掘名称背后的历史故事,联结方言与本土文化记忆;到讲述《上海小吃》“倒背唱词”技巧,诸如“前快后慢”与“重音错位”,“入声字”与“婉转拖腔”,学习短促爆破音与绵长尾音,孩子们投入,连家长也跟着老师念念有词,就差举手要求上台了。
“我们馆很多活动围绕儿童绘本、儿童文学展开,还有物理小课堂、天文小课堂、地理小课堂。80后、90后家长关注小孩全方面发展,不光德智体美劳,还有非遗等,都要了解。”静安区图书馆副馆长潘圣琳总结,“学科之外的知识性活动,家长们愿意为孩子投入。”尽管如此,静安区图书馆与上海滑稽剧团合作,第一次举办沪语学习活动,家长报名之踊跃依旧出乎潘圣琳预期。
潘圣琳的孩子是10后,“他们越来越缺少沪语锻炼,别说一段话,几句话都没法蹦出正确的沪语用词。”潘圣琳旁听邵印冬、赵灵灵等上海滑稽剧团演员给孩子们上课,“小时候,我一直看《老娘舅》,还有王汝刚的滑稽戏,其实大人同样需要沪语文化的熏陶。”
沪语从娃娃抓起,父母言传身教
开学了,沪语童谣唱作人王渊超更忙了,总结自己“全上海跑”地教学,“有的是全年级每个学生都学一年上海话,有的是兴趣班,四五十个学生一直学,还有一些学校通过‘330课后服务’普及上海话。”
他在小学、幼儿园上沪语文化课,也教小朋友唱沪语童谣。“不过,上课与演出有区别。上课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分享传承沪语的重要性,除了唱歌,还讲趣味小故事、文化掌故。亲子音乐会以唱歌为主,加入互动元素,再做有奖问答。”在荣威·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侬好,囡囡》上海童谣亲子音乐会后,王渊超如是说。
《侬好,囡囡》音乐会上,王渊超演唱《黄浦江》,这是今年他为纪录片《浦江之上》新写的歌,以一问一答形式回顾黄浦江起源,“啥个泾?横潦泾。三条河浜一碰头,就有了老底子的东江。东江东江涨大水,没脱农田冲脱房。黄歇浦变成大黄浦,朝北转个弯,抢道吴淞江,才有了今朝的黄浦江。”
“我们的活动不仅针对孩子,也让父母参与其中。”王渊超与赵灵灵有类似观点,教沪语从娃娃抓起,父母言传身教,“小朋友年纪小,不一定全听得懂,爸爸妈妈听懂了,回到家里跟小朋友讲,有兴趣也可以学学唱唱,蛮有趣的。”
王渊超读高中时尝试吉他创作,在大学里组建乐队,拿过《东方风云榜》新人奖。2010年,女儿“小王王”出生,王渊超发现沪语唱童谣哄女儿有奇效。“乖囡覅兴奋,吃饱奶就睏,眼睛覅拨瞪拨瞪,豪嗦帮我睏”,从《乖囡香喷喷》开始,王渊超把上海味道写进歌里。

 《侬好,囡囡》上海童谣亲子音乐会
《侬好,囡囡》上海童谣亲子音乐会
参加上海市民文化节家庭音乐大赛,王渊超创作《苏州河》,讲述上海母亲河的岁月变迁。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小看独脚戏启发了沪语童谣创作,比如《垃圾分类再垃圾倒》借鉴姚慕双、周柏春《宁波音乐家》,用谐音音符构成旋律动机,另一首童谣《光盘行动在身边》有姚慕双、周柏春《新老法结婚》影子。《Me More Say》更是有着独脚戏观众意会的语音密码。
“小王王”15岁了,到了喜欢二次元的年龄。“二次元与上海话、海派文化不矛盾,我吃披萨,也吃大饼油条。她看《哪吒》《浪浪山小妖怪》,也对《黑猫警长》有兴趣老钱庄,后者有上海话版本。只要找到切入点,小朋友会喜欢。”
电视剧《繁花》热播,王渊超把观后感变成《繁花地图》,“从进贤路到茂名路,再从巨鹿路到瑞金路,想要陪侬荡荡马路,看遍大上海的繁华,人人心里侪有伊的繁花。”
“我看上海话版《繁花》,我女儿也跟着追剧,觉得好玩。”王渊超说,“这就像我们带她去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很多时候需要打开这扇窗、播下这颗种子,帮她接触到沪语与上海本地文化,”
 周婉彤在妈妈的鼓励下用沪语说《上海小吃》
周婉彤在妈妈的鼓励下用沪语说《上海小吃》
 周婉彤、潘昊霖等五位学生获得优秀学员证书
周婉彤、潘昊霖等五位学生获得优秀学员证书
 《欢迎入戏》之上海话互动亲子秀挤满了孩子
《欢迎入戏》之上海话互动亲子秀挤满了孩子
在《欢迎入戏》之上海话互动亲子秀,潘昊霖又出现了。他和妈妈从杨浦的家赶来普陀看演出。妈妈介绍,8岁的潘昊霖喜欢做小主持人,从网上扒学习素材,一步步爱上上海话。5岁的周婉彤跟着妈妈从浦东来普陀看亲子秀,她和潘昊霖一样,在上海滑稽剧团与静安区图书馆合办的沪语学习活动拿到优秀学员证书。“学习上海话,还能培养她待人接物大大方方。”妈妈说。
坚持才有众人拾柴火焰高
2018年起,王渊超在闵行区平阳小学上课。“每隔一周上课,这个月给一个班上完,下个月换一个班级。孩子们升到三年级,又来了新的二年级小朋友。”浦东现代宝贝幼儿园是王渊超另一个教学点,“园长买票看我的音乐会,看完以后再找我,‘王老师,我们学校以海派文化为特色,能不能来教孩子唱沪语童谣’,就这样,有20来个孩子一直在上课。”
“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大环境更重视本地文化、海派文化,比如普陀区有几十家幼儿园都在推广沪语。”赵灵灵介绍,上海滑稽剧团与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作为指导单位,参与杨浦区教育局主办的“同济杯”杨浦区中小学生首届沪语达人评选,将在10月中旬揭晓赛果。
《欢迎入戏》之上海话互动亲子秀,定期登陆北外滩来福士演艺新空间,独脚戏《两个人说笑话》、情景戏《弄堂代言人》、互动戏《一首简单的歌》,帮助孩子体验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弄堂游戏,做上海喜剧的笑点发现者、上海游戏的实力小玩家。


 上海滑稽剧团演员在上海各学校进行公益沪语教学
上海滑稽剧团演员在上海各学校进行公益沪语教学
2012年至今,上海滑稽剧团一直进行公益沪语教学,演员们足迹遍布虹桥中心小学、向阳小学、汇师小学、襄一幼儿园、同济中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金山龙航小学等。2022年剧团响应杨浦区教育局、同济中学号召成立同济沪语联盟,共同推进中小学沪语推广,累计课时2000节。联盟学生们的汇演,也是对上滑沪语教研组的考核,滑稽曲调《小八腊子紫竹调》、独脚戏《英文翻译》、上海说唱《礼貌歌》、沪语朗诵《沪语宋词说与唱》、沪语歌《上海谣》,让人目不暇接。
2014年起,上海沪剧院开启沪剧新星养成计划,聚焦4岁至12岁少年儿童,举办学说沪语、学唱沪剧系列训练营。2023年沪剧院“沪剧高阶班”应运而生,择优录取10岁至13岁学生,集中培养念白、乐理、声腔、表演。
 “沪剧高阶班”学生在学习
“沪剧高阶班”学生在学习

 “沪剧高阶班”在浦东新区金海文化艺术中心演出《芦荡火种》
“沪剧高阶班”在浦东新区金海文化艺术中心演出《芦荡火种》
“沪剧高阶班”今年在浦东新区金海文化艺术中心汇报演出《芦荡火种》。第一位上台的“阿庆嫂”徐紫恬只有11岁,4岁时在爷爷启蒙下学习沪剧。6岁时,她与爷爷组队参加第二届浦江沪剧节“乡音和曲”邀请赛,表演的正是《芦荡火种·智斗》,获得少儿组第一名。爷爷自豪地说,“作为上海人,我们有责任将沪剧发扬光大。”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要发挥语言优势,多跟小朋友说上海话。”王渊超掰指头算了算,“小学一星期上四五节英语课,英语水平达到母语水平要学多少年?家里没有语言环境,想让孩子流利讲上海话,有点痴人说梦。孩子听得懂上海话,但是讲不了,做‘哑巴’,等到他们成了爸爸妈妈,他们的孩子都听不懂上海话。过两三代人,传承2000多年的吴语文脉就断了,靠方言传播的沪剧、独脚戏也会被遗忘。”
“没有乡音就没有乡愁,沪语经过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积累了生活智慧,有发展、有融入、有趣味、有生命力,值得被我们保留。”在王渊超看来,沪语传承的意义不止于日常交流,“上海话里,下雨叫落雨,下雪叫落雪,‘落’很有古意,落英缤纷、无边落木萧萧下,古诗有很多充满意境的‘落’。同理,今天叫今朝,衣服叫衣裳,今朝有酒今朝醉,云想衣裳花想容,沪语处处有古意盎然的遣词用句,又非常生活化。”
“唐诗、宋词回到方言中,能感受到韵律之美。”赵灵灵在不同课堂上对孩子们讲起骆宾王《咏鹅》,“沪语保留入声字,类似古代发音,所以《咏鹅》看似不押韵,用沪语吟诵就是押韵的。”
“不说研究沪语怎么形成,为什么有那么多音,你光能够表达出来,让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哪里人,就很有用。”在潘圣琳看来,“沪语是上海人又一张身份证。如果沪语流失了,那么我们与其他城市其实也没多大区别了。”
荣威·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工作人员反复斟酌《侬好,囡囡》上海童谣亲子音乐会曲目,在宣传页推出沪语小考题,比如“饭泡粥”是形容上海早餐、讲话啰嗦还是下雨天,在音乐会外场准备弄堂游戏。“我沾孩子的光,回到了童年,希望下次还有。”来看音乐会的家长说。
“金铃塔,桃花扭头红,杨柳条儿青”“笃笃笃,买糖粥老钱庄,三斤蒲桃四斤壳”“落雨喽,打烊喽,小巴拉子开会喽”,上海小囡从容大声讲着上海话,此刻的他们未必确切懂得沪语如何承载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情感,但在乡音响起的一刻,血脉相连,有了具象的画面。
粤友钱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